中国产能过剩也可造福世界/Project Syndica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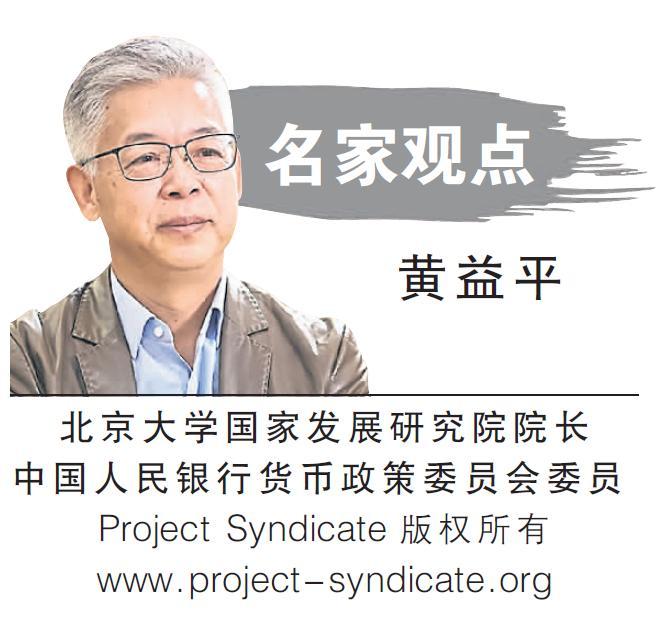
在今年5月于杭州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上,我提出了后来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绿色马歇尔计划”的“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
该计划包括三个目标:协助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扩大中国的总需求以及提升中国的全球领导力。
与当初的马歇尔计划一样,该计划将提供大量商业信贷和投资、政策性贷款以及政府援助。
最近围绕中国主要绿色产业包括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产能过剩的讨论给了我启发。

定义存争议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今年4月在与多位北京大学教授的讨论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两个忧虑:一是中国产能过剩似乎是政府补贴的结果,二是其规模已大到扰乱国际市场的程度。
一个月后,美国宣布了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关税的决定。
对“产能过剩”的定义可能存在争议。正如一些中国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中国企业能够销售其产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那就不存在“产能过剩”。因此如果我们把产能过剩理解为供应超过需求的状况,那么就可以用它来为国内和全球背景做区分。
这里涉及三组因素:宏观经济失衡、显性和隐性补贴以及相关产业的规模。
“国内”产能过剩是中国整个1970年代后改革时期的特征,因为本国生产的产品超过了国内消费量——经常账户的大量盈余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解决产能过剩的第一步就是实现经常账户的平衡。
事实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当局一直在通过刺激国内消费追求这一目标。
不公平补贴?
而美国人和欧洲人更关注显性和隐性国家补贴,他们声称这些补贴使中国制造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不公平优势。但一份2022年发表的工作文件指出,中国在电动汽车方面的显性补贴(包括直接补贴、减税和专有许可)在十几个受调查国家中处于平均水平,而且低于挪威、美国、法国和德国政府的补贴规模。
隐性补贴——即降低的要素成本,则不那么显而易见。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副部长杰伊·尚博在7月发表题为“中国产能过剩与全球经济”的演讲时引用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项分析结果,估计中国的隐性补贴约相当于GDP的5%,是美国、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10倍。
虽然这些数字与我在15年前所做的研究中得出的结果相近,但尚博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者的解读是有缺陷。
禁不规范非法补贴
中国的要素成本扭曲状况不是作为产业战略的一部分而制定的,而是作为一项过渡政策存在,且大部分支持都给了国有企业。
如果要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些在国际上竞争的私有中国绿色科技企业正因为这项政策而处于明显劣势。
地方政府面临财困
尽管如此,地方政府推出的各种“投资促进项目”还是为私营绿色科技企业提供了隐性补贴,例如减免土地使用费用。因此欧盟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补贴致使中国电动汽车的售价要比欧盟生产的车型低20%。
但地方政府提供的支持也在迅速减少,部分原因在于目前许多地方政府都面临财政困难,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中央政府已开始禁止这种不规范的非法补贴。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导致人们对该国产能过剩的影响产生了过度的担忧。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其经济政策又往往将投资集中于某些部门和行业。
这可能会让其贸易伙伴遭遇困境。但问题是中国绿色科技行业的规模可能是一个比补贴更严重的问题。
美中都有绿色马歇尔计划
中国确实需要减少国家指导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并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以确保共同繁荣,这就是我提出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建议的原因。
中国在绿色科技领域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生产能力,但也在发达国家市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壁垒。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在努力推进自己的绿色发展议程。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约1.7兆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资,但截至2022年只吸引了544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外国直接投资。”
所幸中国拥有可以帮助填补这一缺口的技术、产能和资金(商业融资、政策性融资和政府援助),可以借此推动全球绿色发展,促进本国经济,同时巩固其国际领导地位。
有趣的是,在8月底,曾于2021-2023年间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布莱恩·迪塞提出了一个“清洁能源马歇尔计划”,并提及中国事实上也在考虑同样的想法。
理想情况下两国可以在这一倡议上展开合作,但即使中美各自推行独立的绿色马歇尔计划,也依然可以大大加速全球绿色转型。
Project Syndicate版权所有
特朗普、关税和美元的命运/Project Syndicate
作者:马克·布莱斯(布朗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
随着特朗普政府对世界其他国家“疯狂”征收关税,许多评论家担心会出现“为疯狂之举洗白”的问题,也就是给那些毫无合理性的政策赋予令人信服的理由。
他们认为这种无知的做法分散了人们对正在我们眼前上演的骗局的注意力。特朗普家族进军加密货币领域的举动——其发行的meme币俨然一种公开的贿赂邀请——显然支持这种解读。
但这是唯一的结论,还是另有内情?
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另一种解释。
早已放弃自由贸易
美国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方略早在2016年大选时就已经被放弃了——当时唐纳德·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期间都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特朗普随后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商品征收关税,而其中许多关税也在乔·拜登总统执政期间得以保留或延长。
作为拜登标志性政策之一的《通货膨胀削减法》试图促进美国绿色行业的再工业化,而这些行业除了受到特朗普关税保护外还将获得补贴。
特朗普最新出台的一轮关税也是为了推动再工业化——尽管是更为碳密集型的那种。因此自由贸易似乎已不再是两党的选择了。
美元是个大问题
两党都支持保护主义政策的原因在于,美元在推动结构性贸易失衡方面的全球角色。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早在1944年就认识到的那样,如果任其发展,所有国家都愿意成为净出口国而非净进口国。
如今欧盟、亚洲和海湾地区那些净出口国所赚取的美元都无法被本国经济吸收,因为这会提高国内工资和物价,削弱其竞争力。赚取的美元对当地银行来说是负债,而将其转化为资产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购买美国国债,这实际上是将现金交还给美国,使其能够继续购买出口商品。
工业不再是主角
因此,在过去40年间美国通过发行利率为2%的数字欠条,进口了它想要的几乎所有东西,而这些欠条也从未被要求偿还过,因为美国国债也是出口国所需要的储蓄载体。这意味着抛开其他因素不谈,美国是不存在经常账户约束的。
那美国为何要结束这种看似神奇的状态呢?正如马修·克莱因和迈克尔·佩蒂斯所指出的那样,无视经常账户约束实际上会带来一些长期成本。净出口国积累了巨额盈余,但代价是削弱了国内投资和当地工资,从而压抑了经济,而美国“受益”于无限制的廉价外国商品,但代价是掏空了自身的工业能力。
1975年时美国最大的三个雇主是埃克森公司、通用汽车和福特公司;2025年的最大雇主则是沃尔玛、亚马逊和家得宝。前一类企业生产贸易商品,而后一类公司基本上在国内销售进口商品。
鉴于这些长期影响,美国两党的领军人物都开始将美元的“嚣张特权”视为过份沉重的负担。两党都希望通过促进国内生产来“重新平衡”美国经济,这就需要出口国被迫进行调整以减少对美元的需求。

特朗普
不便说出的真相
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一点说出来呢?或许是因为与谈论贸易政策的细枝末节相比,声称“被其他国家割韭菜了”更能打动选民。
此外,虽然特朗普政府缺乏重新平衡全球秩序的全面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秩序的重新调整没有发生。
毕竟德国的出口引擎甚至在冠病疫情前就已经熄火了。它最近放松“债务刹车”(宪法规定的结构性赤字上限)并接纳投资的行为表明朝向国内消费的再平衡已经开始。
中国提早反应
特朗普推动的欧盟国防开支激增将为这一趋势增添更多动力,而欧元区更加由消费驱动的前景将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个可行的美元替代物。
至于中国,它似乎已经意识到,向世界其他国家大量出口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等绿色产品是存在局限性的。中国已经实现了美国市场以外的多元化,而这也增加了对更庞大国内消费的需求。
与此同时,其他以出口为导向的亚洲国家似乎热衷于在美国开店以保持市场准入。
世界再平衡
这样一个重新平衡的世界需要更少的美元。终结当前的体系无疑将带来巨大破坏,而美国再工业化的前景也可能被证明是虚幻的,但重点是要记住两党都认为这是必要的。
再平衡进程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已启动,就算他下台,推动这一进程的力量也可能依然存在。
相关新闻




